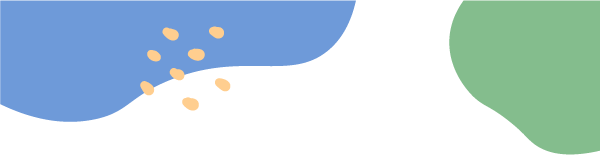


凌晨三点的旧图书馆像一艘沉船。我在古籍修复室第四排书架后,发现了一本没有编号的羊皮书。当指尖划过封面烫金的拉丁文“Si”——“假如”——时,书脊突然渗出淡蓝色荧光。那些光点如同苏醒的萤火虫,钻进我的皮肤。

第二天,世界开始出现“重影”。
咖啡杯沿浮现另一圈陶瓷花纹——在某个可能性里,它是明代青花瓷的残片。地铁玻璃映出两张脸:一张是加班后的疲惫面容,另一张却戴着登山头盔,脸颊有高原红。甚至看见同事身后拖着的“影子”——不是黑暗,而是他若成为画家的模样:沾满油彩的围裙,手中握着不存在的调色刀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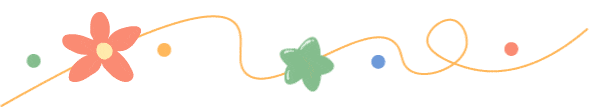
我成了可能性的感染者。
最初恐慌,继而狂喜。那些“重影”并不虚幻——它们有温度、有气味、有重量。那个未能寄出的吻在空气中留下薄荷糖的甜味;那条未选择的职业道路在指尖留下木屑的触感。我意识到,每个“假如”都是平行宇宙投来的漂流瓶,而我意外获得了打捞的能力。
最深的震撼发生在母亲身上。她身后浮现的“重影”,不是记忆里操劳的主妇,而是一个穿飞行夹克的女飞行员,站在四十年前的航校门口,眼里有整个天空。那天晚饭,她忽然说起:“其实我差点考上飞行员,但那时候觉得女孩子该安稳些。”她不知道,她放弃的那片天空,此刻正以淡蓝色的光影形态,温柔地笼罩着她的白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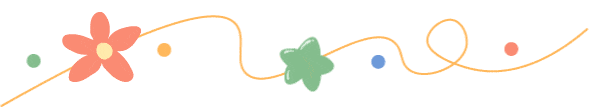
我开始记录这些“重影”,在笔记本上绘制“可能性地图”。发现越是重大的抉择点,分裂出的“重影”越清晰;而那些日常的、微小的“假如”——假如多读一页书,假如对陌生人微笑——则像薄雾,却数量惊人。原来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棵树,而是一片不断分岔又交织的发光菌丝网络。
奇妙的是,“感染”具有传染性。当我向好友描述她身后那个成为战地记者的“重影”时,她突然流泪:“昨天我差点报名国际志愿者。”她眼里的光,与那个“重影”手中的镁光灯,在某一刻完全重合。可能性在共鸣中获得了某种真实性。
我开始理解,这本羊皮书不是魔法,而是催化剂。它激活了人类固有的潜能:我们本就活在无数可能性的叠加态中,只是日常意识将其压缩成单一现实。那些“重影”从来都在,是我们自己选择了“看不见”。
现在,我站在图书馆的窗前。城市灯火在雨中晕染开来,每一盏灯后都飘浮着无数“重影”——未写的诗,未启程的旅行,未说出口的爱。淡蓝色光点正从我掌心飘出,像蒲公英种子飞向沉睡的街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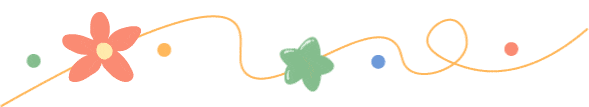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,当第一粒光点落入某个失眠者的眼睛,这场温柔的“感染”将真正开始。我们将重新发现:现实不是坚硬的石碑,而是无数“假如”汇聚成的河流。而人类最壮丽的创造,或许不是实现了哪种可能,而是终于看见——所有可能性,都同时为真。
羊皮书最后一页缓缓浮现新的文字:“你不是看见可能,你成为了可能。”
窗外的雨,忽然开始向上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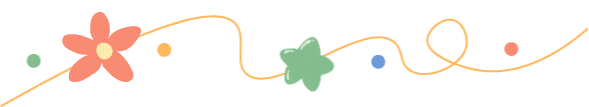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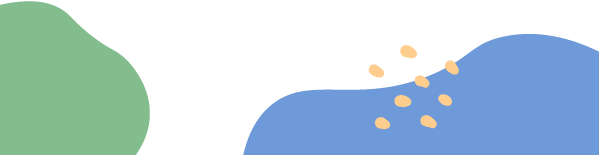
 ༺摸鱼村এ 海风〰️ ༺摸鱼村এ 海风〰️2025-12-06 20:21:01 |
